第三期“百书阅读 百场讲座”之九
发布人: 时间:2020-12-07 浏览次数:3619次
12月3日下午,沙红兵教授在图书馆504会议室带来了题为“王维的创伤书写——《王维诗集》导读”的讲座。这也是广州大学经典百书阅读推广中心、图书馆和人文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三期“百书阅读 百场讲座”的第九场讲座。
沙红兵,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文与诗文理论研究,特别是唐宋诗文与晚清诗文研究。出版《唐宋八大家骈文研究》等专著,主持国家及省市社科研究项目多项,曾获广东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

沙红兵教授
沙红兵教授首先介绍了凯西卡鲁斯对“创伤记忆”的定义,即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其中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反应往往是延宕和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沙红兵教授指出,作为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王维十分重视忠君、名节。在王维作品中有属于自己的创伤记忆的书写形式,创伤记忆在其诗文中反复出现,如《重酬苑郎中》“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惭未报主人恩。草木岂能酬雨露,荣枯安敢问乾坤”,《与魏居士书》“偷禄苟活,诚罪人也”,《责躬荐弟表》“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已至今日”便是他内心的表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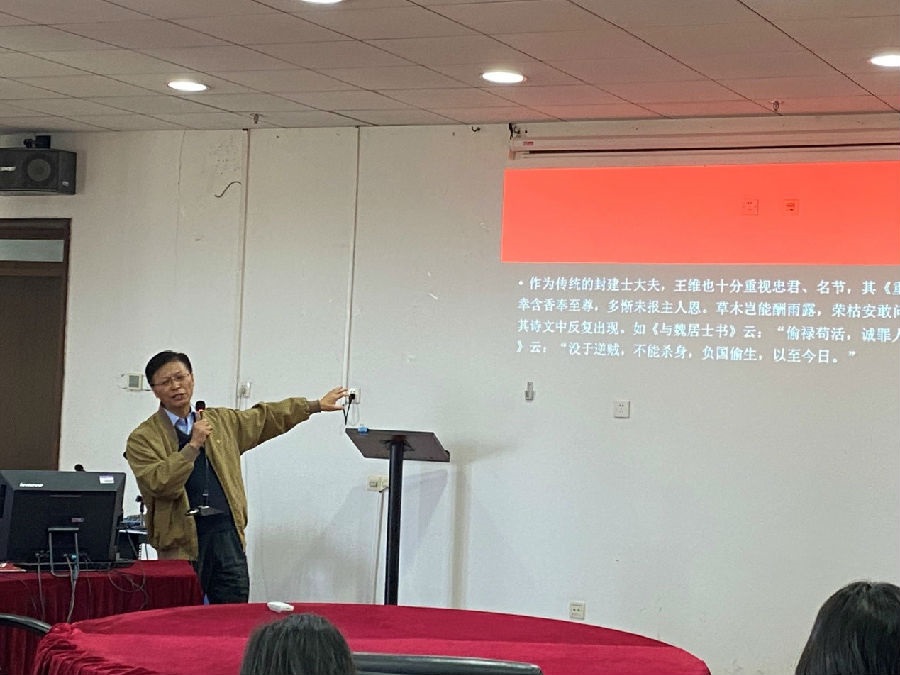
沙红兵教授讲座
沙红兵教授认为王维诗的创伤书写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模式是从对面写起,或让他人从他处来看自己。如王维《山中寄诸弟妹》中的“山中多法侣,禅颂自为群。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两首诗的共同点就是从对面写起,前一首是“身在山中,却从山外人眼中想出”,后一首则“不说我想他,却说他想我,更加凄凉”。而他的诗“吹箫凌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则说黄昏送客,以湖舟的客人眼光回看岸上。在这些诗中,王维让他人从他处来看自己。这种从对面写起或让他人从他处来看自己,实际上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此处与彼处之间,既拉开一定的距离,又在这一定的距离之外,远远地、静静地仔细端详和打量,造成两者之间既离又合、似合又离的特殊效果。
王维诗的另一个表现模式是从一定距离之外,回看、遥望的场景描述,与前面所讲的从“对面写起”十分类似。如《观猎》一诗中的“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云,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就是这种模式。
王维在《为薛使君谢婺州刺史表》中写的是薛姓友人,但除了陕州地方官的经历不同以外,其余也都是王维的亲身经历,同时也正因为写的是友人,是从对面、从一定距离之外写起,王维大胆、直率地写到了当日受尽威逼的场面,这是他在单纯写自己的诗里不敢直视、不敢辩白的。
君臣大义所负愈重,王维也愈不堪安史之乱所带来的创伤记忆之煎熬,最后竟归佛、归隐,便留有《叹发白》中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等诗句。

讲座现场
沙红兵教授指出,王维在直接涉及到自己的诗文中,对创伤事件往往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且只表示戴罪有愧,不作或少作辩白,至多如《谢除太子中允表》所云:“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踞天内省,无地从容。”卡鲁斯说,创伤记忆会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方式反复出现,在王维的诗文里,创伤记忆的确反复出现,但不是通过幻觉的方式。在直接与相关的诗文里,王维只悔罪不辩白。在为与自己有相似遭遇的他人所写的表,碑、铭等作品里,他不仅悔罪而且在对当年的残酷场面的展现中巧妙地为他人和自己辩白。王维习惯从对面,从一定的距离之外写起,这不仅是“作法”问题,还应该是王维观察世界与人生的一种立场与态度。近年来,在文史哲及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对所谓“创伤记忆”的研究似成一种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学里,像王维的诗文,其实也可以提供类似的见证,而且是十分微妙的见证。




